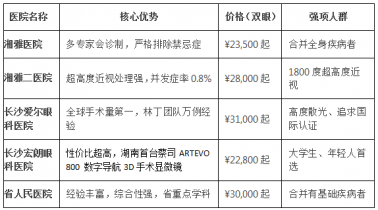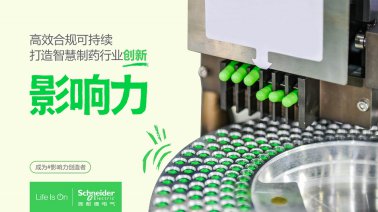纳粹禁烟史:二手烟是优等民族之大敌(2)
有了科学理论撑腰,当局推动强制禁烟时便更理直气壮了:此前,在车间、电影院、学校等公共场所,老烟枪们可以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现在不行了;警察和公务人员如果身穿制服,是万万不可抽烟的;即便是做烟草广告,也要受到种种限制,凡是试图将吸烟描绘为无害,或将吸烟者描绘为有男子气概的广告,均在当局封杀之列……
作为“优秀雅利安人”的孕育者,女性被禁烟令格外小心地“呵护”起来:在咖啡馆等公共场合,兜售女用香烟被严禁;25岁以下、55岁以上的女性以及孕妇都不配发香烟配给券,并限制摊贩将香烟零售给她们;针对女性的反烟草电影广为播映,报纸频频刊载讨论吸烟及其影响的社论;有些地方甚至声称,将开除在公共场所吸烟的女性纳粹党员……
即便是在前线拼命的德军士兵,也不得不接受每人每天6根香烟的配给供应。身处枪林弹雨下,这么一丁点儿供应量,即便在那些烟瘾不大的人看来都嫌太少。因此,前线军人想要在激烈的战斗之余抽根烟放松紧绷的神经,常常免不了事先精打细算一番。
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
拜纳粹宣传机器的高效运作所赐,烟草在当时的德国俨然成为“人民公敌”,希特勒也亲自出马,大讲特讲他戒烟成功的“光辉事迹”,把抽烟与否作为区分“正邪”的标识。他说,德国的盟友,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弗朗哥都不抽烟;而与德国敌对的英国、苏联和美国,其领导人丘吉尔、斯大林以及罗斯福都手不离烟,表明他们“堕落至极”。
彼时,在纳粹的话语体系中,假“元首”之名劝他人戒烟颇为流行。按照普罗克特在其研究中的说法,如果对方是个烟民,纳粹党员最常用的是下面这样的说辞——
元首他本人就反对吸烟,并认为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戒掉这种恶习。我们无权利用这种玩意儿来损害我们自己的健康。我的国社党兄弟,这些你都知道吗?
宣传戒烟理念的同时,还有专业人员为老烟枪们提供心理咨询。另一项与之相关的发明是含尼古丁成分的口香糖——犯烟瘾时,咀嚼一块便有舒畅身心之效,此后可通过逐步减少尼古丁的摄入量,最终成功戒断烟瘾。还有一款功能类似的产品名唤戒烟漱口水,其中添加了硝酸银,用它漱口之后再抽烟,会觉得烟味非常令人恶心,反复多次之后即可戒烟。

凡事都有两面。希特勒口沫横飞地将烟草称为“毒品”,可纳粹德国在国内大力推行戒烟的同时,并不敢将烟草贸易列为非法,原因无非是,这门生意可提供丰厚的税源。
普罗克特注意到,到1941年,烟草业的税收在纳粹政权的财政总收入中占了5%,比重不可谓不高。就在同年11月3日,当局颁布了一道法令,将烟草税提升至香烟零售价的90%,这一惩罚性税率的最大获益者依然是德国政府,令后者得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行。
战争废墟上,“复吸”蔚然成风
虽然谈不上令行禁止,纳粹德国的吸烟者比例确实连年走低。从1939年至1945年,德军士兵消费的香烟数量同样逐步减少,一项于1944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相比二战前,虽然德军中烟民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在战争期间,每名军事人员每年的吸烟量下降了23.4%,每天吸烟超过30根的人的比率更是从4.4%跌落至0.3%。
当然,考虑到彼时的环境,很多人并非真心与烟草决裂,而是因为物资短缺,不得不“减量”,或者是慑于上峰压力,在接受调查时提供了虚假信息。希特勒的女秘书戈尔达·克里斯坦曾回忆称,柏林战役末期,“元首地堡”内散发着一股空虚的气氛,原本对希特勒有所回避的人公开吸烟,希特勒自杀后,大家更是无所顾忌地吞云吐雾。
希特勒之死宣告纳粹政权的禁烟运动进入尾声。主管此事的卡尔·埃斯特尔,也因害怕遭到清算而自裁。根据普罗克特的说法,埃斯特尔在战时参与杀害的人数多达20万。
第三帝国土崩瓦解,“反对烟草学院”关门大吉,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上,吸烟现象再度兴盛起来。来自美国和瑞士的香烟,经由黑市源源不断地运抵德国。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香烟甚至被作为援助物资免费输入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