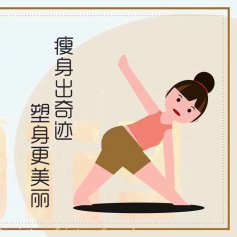霭理士与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创始人桑格的故事(2)
1915年的新年午夜,霭理士与玛格丽特以一个“午夜之吻”开始了新的一年,开启了绝望旅程中的希望之旅。不久,玛格丽特就频频邀请当时已德高望重的霭理士支援她倾注一生的计划生育事业。
早在1914年3月,玛格丽特就创办了《女叛军》(The Woman Rebel)杂志,向女性传授避孕知识,此后她又创办《计划生育评论》(Family Limitation),教育大众“孩子可是个珍贵的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支付得起。曾专门写过一本《欧洲的天才》探讨人类科学的霭理士,对于“优生学”向来有着青睐,他为《计划生育评论》撰写长文,阐述计划生育不仅有助于抑制人口的过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培育出更为健全的民族人种。不过,对于“计划生育”这一话题,霭理士的话很快说尽,此后玛格丽特多次邀约霭理士发表看法,均遭婉拒。似乎没有人能够逼迫他做任何他不情愿的事。伊迪丝回到英国后数番劝说丈夫与自己同行前往埃克斯(Aix),1902年时伊迪丝曾在那里恢复了健康,因此她迷信重回埃克斯会使她枯木焕春,然而霭理士无动于衷。
伊迪丝的情绪与胸襟貌似跟随着她病情的反复而不断变换。不久之前,她还誓与玛格丽特结成莫逆,为了与玛格丽特会面,她重金订下了一间豪华餐厅,然而留给玛格丽特的印象却是一个“极端自私、无比苛求的女人”。及至她神经衰弱幻象四起,她开始恶作剧地在朋友们面前公然谈论霭理士那些难为情的隐私。医生建议霭理士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这让她产生了更可怕的受害臆想症。短暂的照顾之后,霭理士再度放弃了作为丈夫的责任。尊严丧尽的伊迪丝这一次收拾起了她无助的哭嚎,捡起她最后的骄傲,她要求彻底的剥离——离婚。他们25年的婚姻平静完结,然而一切都没有改变,伊迪丝离婚后仍佩戴着结婚戒指,他们仍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彼此的生命里。
1916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霭理士去探望病中的伊迪丝,她还兴致勃勃谈论重去美利坚的计划。临别时,她怕传染不让霭理士吻她的嘴唇,霭理士拉过她苍白的手背亲了一亲。待他接到病危通知,再次赶到迈达山谷时,伊迪丝已陷入了深度昏迷。手背上的那一吻,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吻,他们一生的情爱实验最终定格在了这个“同志之吻”上。
霭理士:被女人们分享的暮年
希腊悲剧的天才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接受且乐于呈现矛盾与冲突,并欣然领会人生绝没有出路。伊迪丝去世以后,霭理士度过了被众多女性分享的晚年。他拒绝为任何人写序,拒绝出任公职,拒绝参与公共政治,却从不曾拒绝任何一封来自欧洲或遥远美洲的妇女来信。每天都有数量庞大的新鲜的痛苦向他涌来,等他施以援手。女人们苦闷的独白、隐秘的梦境、私藏的裸照、哭泣的灵魂,纷纷扑向他广阔的胸襟——在那片开放的墓地,男人和女人间永恒的战争被自然所拥抱,获得片刻安宁。
女人是霭理士一生钻研的科目。他至死热爱女性,尤其是“困难的”女性。他晚年曾在情书中,如一个爱情里的堂吉诃德般表白:“正是你提供的难题,让你完美。我从未爱上过一个简单的女性。” 弗朗克丝,一个将自己的全部梦境贡献给霭理士的女人,成为了他的最后一桩事业和标本。霭理士那些叫板弗洛伊德的有关梦境的著述,很多素材都来自这一位他人生最后的守护者。他们毫不逊色的故事,又是另一番话题,本文不再涉及。1929年初,玛格丽特·桑格写信给弗朗克丝道:“我希望把你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亲爱的霭理士。”她建议弗朗克丝辞掉自己的工作,而她将担负起她损失的全部薪资,这样弗朗克丝便可全情投入照顾年事已高的霭理士。
弗朗克丝欣然接受了这份赠礼。暮年的霭理士,在这位带着两个儿子的法国女人的陪伴下,不辍地进行人类情感内在构成及其本质的探索。最终霭理士也没能给予她婚姻。他去世以后的声名湮灭,与二战后“优生学”被集体驱逐出学术圣殿有莫大的关联。作为鼓吹“优生学”的悍将旗手,霭理士信仰“创造最好的个体,以创造最好的文明”。他晚年对种族惨案置若罔闻,并不反对将艺术审美与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于纳粹有某种意义上的默许。霭理士于1939年走完自己的旅程,结束了一种美学生命,抑或辉煌人生的强烈的尝试,并未亲眼看到法西斯制造的人间惨剧。
“每一条路都可以深入世界的神圣神秘”,同样,每一条罪行亦是通往秘境的幽深巷道。当审美情绪集体噤声,我们首先应当讨论的是艺术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