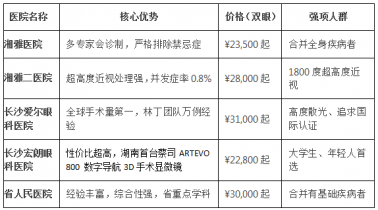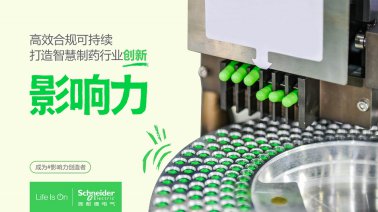两次高考 一个目标(2)
我哥在1978年的高考中也顺利被泸州医学院(即现在的西南医科大学)录取,而当时四川录取率也只有5%左右。在接下来的几年,我的两个妹妹又分别以高分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这在当地传为佳话。为此,我们也经常感慨这是“文革”后期父母对我们严格要求的结果。
在战伤救治中成长
之前我以为我的高考成绩是很高的,到了学校才发现,我这只能算是中上等水平,好几个同学考试分数都超过了400分,真是山外有山。
作为“文革”后军队院校首批正规大学生,我们军医系分为两个大队:一个是平均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从军队考上来的学员,另一个是我们应届高中生或当过知青考入大学的同学。尽管同学们年龄相差比较大,大家基础参差不齐,但学习劲头都很足,都渴望有比较多的时间用于专业学习。
在大学初期我对专业选择没有特别关注,只想好好学习,当一个合格的军医而已。
对战伤的最早认识除来自于小时候“文革”中看见因武斗造成的伤员外,直观的体验则来自于1979年3月在学校参与的对云南前线后送伤员的转运工作。记得那年春节前后,我们就隐约听说云南边境要发生一些事情,但没有确切消息。初春的一天,我们全体学员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到学校大操场集合,这才知道云南前线发生了自卫反击作战(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越边境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有部分伤员需转运到后方医院治疗,我们这批学员要参加将伤员从重庆梨树湾火车站转运至第三军医大学3个附属医院的工作。由于当时的我们还缺乏对战伤救治基本知识的了解,就在大操场紧急学习了战伤救治四大技术,即止血、包扎、固定和后送(当时还没有包括通气这一基本技术)。我记得课程是由西南医院骨科著名专家吴先道教授讲授的,他讲课通俗易懂,针对性强,使我们初步了解了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在后来的伤员转运中得到了应用,使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时任国家副主席乌兰夫来重庆视察时的亲切慰问。
大学毕业留校后,我希望到一个与军事医学更加密切的单位去工作,这样我便去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在专业选择时,我考虑我的兴趣在外科学,特别是与战创伤救治密切相关的野战外科学,所以就选择在野战外科研究所继续学习和工作,之后又开始攻读野战外科学的研究生。
1984年,云南边境老山地区战事再起,当时我已到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工作快两年了,工作的重点一方面是了解各种现代武器对人体致伤机理,同时也研究如何预防和治疗这些损伤的策略和方法。当老山战事再起时,我和3位研究生同学积极要求去前线锻炼,获得了组织的批准。为此,我曾经4次去前线参加战伤救治与战伤调查。记忆深刻的,除了刘荫秋教授和王正国教授等前辈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外,还有3件事至今难忘。
一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向战士们讲解防地雷鞋的防护原理并指导他们使用。为此,我在老山前线生活了一段时间,常常深入一线作战部队手把手地教战士使用。根据后来的反馈,防地雷鞋的使用对战时地雷伤的防护和战后的排雷工作起到了重要保护作用。虽然前线危险且条件艰苦,但通过这项工作能保住战士的生命,我感到非常快乐。
二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即关于滤色清创眼镜的研制。当时,我通过参考文献和相关研究发现了不同活力组织对光的反射在600(纳米)以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生物现象,根据这一发现,希望尽快研制出这种滤色镜,从而帮助外科医生进行精确清创。那是在1986年底,我去四川华蓥山的一个兵工厂试制滤色镜片。那家兵工厂位于大山深处,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打听错误,我费了一整天走了两次弯路,才在下午5点左右到达广安县前锋镇。谁知到那一打听,这个厂是在离前锋镇还有10余公里的华蓥镇。而那时没有去华蓥镇的班车,迷茫中,一个40多岁农民打扮的人说他的家就住在华蓥镇,知道工厂的位置,问我是否跟他一起走山路。无奈中,我只好决定跟他一起走。当时天色已黑,为防万一,我手拿一根树棍,跟在他身后2~3米的距离,一路上提心吊胆。好在这一路没有发生意外,感谢那位好心的农民。当晚上10点多到达华蓥镇时我已浑身湿透,像水淋了一样。由于高度紧张和劳累,我第二天就出现了重感冒,但还是坚持去工厂找到了适合于做滤色清创眼镜的光学玻璃,并简单加工了两副带回重庆。这项研究使我获得了1990年度的国家发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