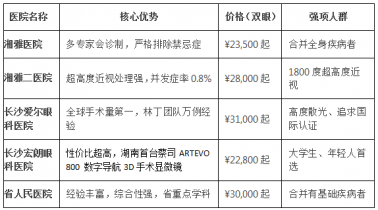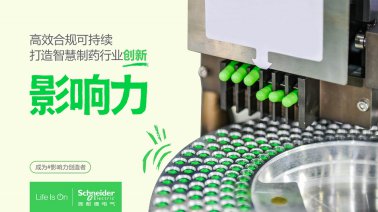两次高考 一个目标(3)
三是一个严峻的时刻,即在老山前线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1987年仲夏的一天,一批伤员被送到野战医院,其中有个战士处于昏迷状态,血压非常低,我看了后初步判断是内出血,经穿刺果然发现有活动性出血,因此急需开腹手术。这个战士为O型血,当时野战医院已经没有O型血了。时间就是生命,由于我是O型血,我便提出我来献血。当时在场的医院院长坚决不同意,说我是来参战锻炼的,是研究生,是客人,万一出了问题他们难以向大学交代。我说到了前线就是一样的战士,一样的医务人员,我为这个战士献血理所当然……经过一番争执,院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其实,献出300ml鲜血对我来讲只有一点损失,但对挽救战士的生命却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经过老山前线血与火的考验,进一步增强了我对前线将士战斗和生活环境的认识和体验,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升华。我常常在想,作为军人和军医,难道还有什么比救治战士生命更重要的吗?没有!军人的责任在保家卫国和人民,而军医的责任在于保护战士们的生命。
从老山前线到科技前沿
作为老山前线参加战伤救治任务的延续,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要显著提高我军战创伤救治水平,光靠热情和干劲是不行的,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开拓创新,特别是在战创伤救治理论和关键技术建立方面尤其重要,而生物高新技术是重要领域。
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们就开始系统研究以生长因子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对战创伤治疗作用。1991年,我编著出版了国际上第一部有关《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的学术专著。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严重战创伤导致内源性生长因子含量减少现象,并阐明外源性应用生长因子加速战创伤修复的相关机制。在国内同道的共同努力下,研制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用于促进急慢性战创烧伤创面修复的基因工程国家一类新药,实现产业化和在临床推广应用。相关结果于1998年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后,被BBC以中国人“把牛的激素变成了治疗烧伤药物”进行高度评价。成果获200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基于生长因子对组织修复和再生的系统研究,我领导的团队又进一步发现并在国际上首先报告了表皮细胞通过去分化途径转变为表皮干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现象。结果于2001年再次在《柳叶刀》发表,为组织修复和再生提供了原创性的理论根据, 被国际同行以“相关研究对细胞去分化给予了精彩的总结”和“是组织修复与再生的第四种机制”等进行充分肯定。根据这一原创性发现,2007年我们在国际上首先利用自体干细胞再生汗腺获得成功,为解决严重战创烧伤患者后期的出汗难题提供了基础,被国际同行评价为“里程碑式的研究”。部分结果获200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疾病谱的改变,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俗称溃疡)防控已经成为国家重大需求,同时也是国际上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我们敏锐地认识到这一转变,并迅速把军事医学科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老百姓面临巨大痛苦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我们发现并在国际上报告了中国人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的主要病因已由创伤为主转变为以疾病(如糖尿病)为主的新特征,阐明了体表慢性创面难愈合的相关机制,创建了包括采用光子技术在内的5种治疗复杂创面的关键技术,显著提高了治愈率。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系统的培训体系,并在全国倡导建立了300余个创面治疗专科(中心),对复杂难愈合创面开展专科治疗,使广大创面患者直接受益。相关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国体表慢性难愈合创面创新防控体系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国际同行以“向东方看”进行高度评价。成果获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40年弹指一挥间,我自己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到接近花甲,从一名战士成长为对国家和军队有一定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回首40余年的经历,特别是高考时的选择,我可以自豪地说,岁月在变,人生在变,但是我高考时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没有改变,并且是始终沿着当时确定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但更多的是作为军人的自豪和救治战伤的责任,目标明确,初心不改。
《中国科学报》 (2019-02-22 第5版 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