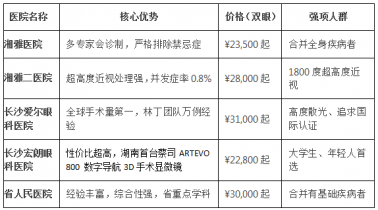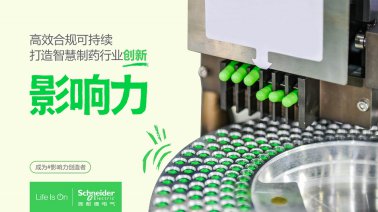互联网医疗没有梦想(2)
李天天看到,常见的互联网打法碰上医疗走不通。“走多少步兑换奖励,问多少问题有补贴,一旦奖励、补贴一停,产品的用户量、活跃度就是断崖式的下降。”
巨头同样成为创业途中的大山。分食互联网医疗蛋糕不仅有创业者,还有BAT ,以及商业保险巨头,平安集团就是一例。平安集团“扶上马,送一程”的策略,令平安好医生在成立仅4年的情况下,弯道超车,率先在丁香园、春雨医生、微医、好大夫之前,完成IPO上市。
一场相互被打断18次的对话互联网通行流量模式失灵,基础的“轻问诊”模式亦被质疑。
2015年年底,春雨医生创始人、前CEO张锐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有过一场对话。张锐代表了风口上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王杉代表了处于垄断地位的传统医疗。
这是一场被相互打断了18次的对话。春雨医生现任CEO张琨告诉AI财经社,“那是鸡同鸭讲,两人完全不在同一个频率。”
王杉直接否定了网络“轻问诊”。他认为,中国移动医疗的商业模式现在根本不存在。根据中国现行的医政管理办法,所有的医务人员必须在医疗机构执业。“如果不在医疗机构执业,严格讲是违法的”。
“IT人想替医生看病,这出了大问题”,王院长有些激动,声音洪亮。他坚持医疗的两个原则是医疗质量和病人安全,强调医疗以医院为场景,以医生为核心。
在他对面,互联网医疗的开拓者张锐认为,互联网医疗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控费为中心,越来越往塔基走。
在对话当场,主持人、医药专家刘谦说,“我觉得这样的对话特别好,过去的问题是院长和移动医疗不对话,因为院长觉得移动医疗玩的都是小儿科。移动医疗觉得院长不愿意尝试新生事物。”
可是,终究谁也不能说服谁。

“互联网想改造医疗,医疗不接受互联网。”张琨认为,这场对话折射出当时传统医疗与互联网医疗难以对话的尴尬,本质上是安全和效率的矛盾。
王杉在那场对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张锐发言不多,语气和缓,甚至有点悲情。
“从今天的发言时间也可以看到,也许就是今天中国的传统医疗机构和互联网医疗所占的位置对比。中国的互联网医疗也许就只占1%,就像我今天在这个论坛上所占的发言时间一样。”张锐说。
真正的悲情故事发生在之后。2016年10月5日晚,张锐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北京去世,享年44岁。他留下了一个“颠覆医疗”的宏愿,自己却因为疾病离去。当时,春雨正在进行的IPO计划也被搁浅。
张锐代表了一批在黑暗中摸索光明的互联网医疗创业者。妻子形容他是一颗火球,燃烧着自己的小火球,扑到了完完全全的黑暗里。
“这个行业层层包夹,重重限制,前路凶险,退路已绝,还伴随无限量低成本的嘲讽和质疑。”在悼文里,春雨医生内容总监顾晓波称,作为行业先行者,张锐一开始就已经选择了地狱难度。
据《健康管理蓝皮书:中国健康管理与健康产业发展报告(2018)》,2017年我国医疗服务的门诊量估计超过80亿人次。
与之对比的是,今年,春雨医生的日均uv达到200多万,意味着一年内将有7亿人次以上访问春雨医生的页面——仅仅是浏览,还不是消费人群,尚无法达到全国门诊量的十分之一。
由政府提供的、有社保覆盖的、非营利性的线下医疗服务,仍是我国绝大多数患者的首选。
来自波士顿咨询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医院数量上,民营医院占比达到56%,公立医院44%;但在住院患者数量上,民营医院仅占16%,公立医院84%。
2017年,《关于征求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和关于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划分了核心医疗和非核心医疗,鼓励互联网技术在“诊疗核心业务以外”的实践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