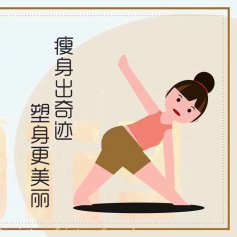五四运动再回首: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和反传统思潮(2)
当然,我们多少还是可以接受这种后见之明。那还是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也许不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近代”。我们从不同角度看,“近代”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观念的,不同的“近代”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而它们各有各的起点,并不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队伍一样,步伐整齐。其次,一个社会进入近代,是一次性的还是多次的累积?按照过去通常理解的那样,“近代史”就是一次性的。也许这个过程拖得时间很长,有拖沓,有反复,但一旦进入“近代”,就一往无前。然而,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中国在不同层面的问题上,曾经不止一次地、跨入不同的“近代”或“准近代”?有时走入“近代”,又出来了(等下次进入的时候,也许已经是另一种“近代”了);有时有些层面“近代”了,但又和另一些“不近代”的层面相互作用,产生了变体。如果宋以来的中国是一种“近代(世)”,18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又进入了另一种“近代”,那么晚清以来的中国史,就不能只从一种“近代”视角来看,不妨看到两种不同“近代”的互动,那这样也许就得把我们的思路调整一下。当然,这个问题我也还没有想清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重要的不是中国“近代”的起点究竟在何处,而是对“近代”概念的反思,试着想一想除了我们认为不证自明的那种“近代”,事情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经济观察报:在《历史·声音·学问》的序论中,您认为中国文化“不是永无变化的单质晶体”,文化自觉不是“复古”与“排外”。近些年来,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开始逐渐反思“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的影响,认可中国文化本位基础之上的国家转型。然而晚清以来的革命者,如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都有着传统文化训练的基础与深厚的小学功底,您认为中国古典的文化资源对中国近代的革命者与反传统思潮有着怎样的作用和影响?
王东杰:您所列举的几位,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都曾在一定时段里反过传统,也曾在另一些时候礼赞过传统;其实,即使那些态度更加激烈的新文化运动者,比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也有这两面性。反过来,一般目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陈寅恪、吴宓,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方面,也都曾有过犀利批判。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他们的某些言论,要知道每一言论都有特定语境,必须放在这种语境里,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另外,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只有理性没有情感的机器。20世纪中国的反传统主义者,往往有理智和情感乃至情绪的两面(但不是都像列文森说的那样,是在情感上依恋传统,理智上否定传统)。理智和情绪常常混在一起,可毕竟是两种东西,情绪高度地依赖于特定时空,理智则相对稳定。后来的研究者面对它们,可以做出区分,不能把情绪性的表述当作纯理智的断言。
中国古典文化资源在近代反传统思潮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王汎森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对此做过精彩研究,他的《章太炎的思想》和《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就是分别讨论章太炎、刘师培的。我个人关注过一些具体的点,比如儒家的“反求诸己”这个道德信条,怎样有助于近代中国人展开文化反思和自我批判。所谓“反求诸己”意味着,出了麻烦,我们首先需要检讨自身有没有问题(注意,这不等于要否定社会批判的必要性。孟子是“反求诸己”的具体阐释者,也是汤武革命的拥护者);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实现自我突破,用章太炎阐发的佛教观念,就是“依自不依他”。这实际上是双重自信:自我拯救是一种自信,自我批评也是一种自信。今天很多喜欢讲文化传统的人则恰好相反,总觉得我们的问题都是外来因素造成的,只要把它们驱赶出去就好了。丢弃了反求诸己的能力。
当然,我并不是说外来的都是好东西,但那和把外来的都当作坏东西,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另外,这些文化本位论者大都表现出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忘掉了民族主义是近代西方的一种发明(这一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得很清楚),这不是典型的“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吗?思维方式都被人换掉了,自己还不知道,把中国文化越讲越窄,越讲越没有前途,起到了“第五纵队”的作用,还自鸣得意。其实,与其天天空谈传统,乱讲国学,还不如真正读点古书,也读点今天的书、西人的书,让自己的思考资源更丰富,才是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