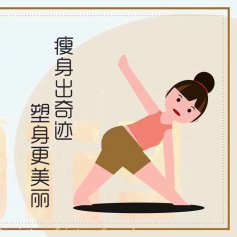五四运动再回首:中国知识分子世界观和反传统思潮(4)
然而,麻烦的是,人民既是革命的主体,又是被启蒙的对象。这就使得您所说的出身于“底层平民知识分子”的领袖成为必要和可能。革命要动员人民,就得要人民听得懂。这不只是个口音、语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贴近人民的想法和生活。这时候,不是胡适这种留洋回来的“大知识分子”,而正是一些贴近民众的基层知识分子,成为合适人选。这种位置赋予他们两重力量:相对于知识分子,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群众”的代言人;对真正的下层民众,这些人的地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识文断字”的本事。他们掌握着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既不完全是“民间文化”,也不完全是“精英文化”。打个比方,这种文化既不是“文言”,也不是“民歌”,而是“语体文”、“白话文”,以“文”传“话”,就是这场“声音革命”在文字层面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声音革命”就是整个中国近代革命的一部分。
经济观察报:在《贯穿于“疑古”与“释古”之间的“故事”眼光》中,您关注到古史构成学说的源流与观念之间的交锋,顾颉刚有将传说化为史料的想法与实践。在后现代史学不断发展的今天,历史也被区分为神话、传说、事实三种不同的层面。您认为这对于以史料搜集、考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解释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构成挑战?
王东杰:当然。这个挑战真真切切。在今天的历史学界,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能和当年的兰克学派一样自信可以“复原”历史了。经过后现代主义冲击,一方面,今天的历史学家较之以往要更加谨慎,会更加自觉地审视史料的来源、构成、生产和流通等对其所包含和传递信息的影响,避开各种可能的陷阱;不过另一方面,在前辈看来,今天的历史学家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更加“放肆”:使用的史料更广泛,包括小说、神话在内的虚构作品,都可以成为探寻往昔的线索;在观念上,更自觉地秉承文化多元论,力图平等对待参与历史的各方,描画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与影响;反对本质主义,更充分地考虑历史中模糊、动态的面相,采用更富弹性的表述;承认历史论述的建构性和多元真实的可能,不把自己的论述当作历史的唯一可能。
然而,这也不意味着真实和虚构之间的界线就可以随意抹去,也不等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此失效。我们仍然需要搜集、考辨、理解史料,并借助于它们思考其背后更宽广和深邃的历史场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研究者应该感谢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因为它使我们想得更多、更深、更细,而不是彻底摧毁这个学科。事实上,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的质疑,使我们离传统历史学家的理想(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更近,而不是更远了。
经济观察报:大众对于历史的记忆源于教科书与世代相传的传说,东亚各国对于历史教科书的修订问题常常有着大相径庭的解释。而历史记忆也常常成为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助燃剂,您认为历史学者在面对大众进行的历史书写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历史学者如何看待自身的公共属性?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能否可以修正大众对于历史的想象?
王东杰:首先,历史学者接受了社会的“供养”,自应回馈社会。可是它不应是对“供养人”的谄媚和讨好,而是要提供禁得起严格学术验证的“真相”,尽管这真相有时恰好和它所在的社会中所流行的说法相反。必须修正公众的历史想象,当然不免招人嫉恨。这时,就像梁漱溟先生说的那样,需要接受者有点“雅量”。公共史学不是历史学者一厢情愿就能收效的。
其次,历史学工作者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社群,对于同一个问题,往往争得不可开交。观众有时搞不清楚,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历史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小姑娘,任人打扮”,既然你们自己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让我们怎么相信?不只是“大众”,很多“小众”也是这么想的。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知识探索,重要的是研讨过程,还是只要一个答案?只要答案,在教育中,不就是死记硬背吗?可是大家好像又很看不起。然而,又不想参与思考和讨论,或者缺乏足够能力(包括知识、方法),想参与而不能。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表明中国人需要的是基本的史学思维的训练。在这方面,专业的史学研究者当然有责任。如果是前一种情况,那危机就不只是历史学所面对的。而是整个社会的。
第三,要专业史家常常“面对大众”,是不现实的,尽管不是全不可能。专业人士当然应该尽可能地平易近人,让更多读者能看得懂,但这不是必然的义务,因为他们的本职并不在此。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少的是“非虚构作家”。他们有能力将专业史家的讨论加以转化,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个要求并不比做专门研究低,甚至可以说是更高。既要有严谨的专业训练,又要有亲民的文笔,而且不是插科打诨,是要提供有趣而且有深度的智识产品。兼具所有这些素质于一身的人很难得,不过这恐怕才是历史学回馈社会最有可能也最有效的方式。